刘汉俊
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,中华诗词是最为芬芳的一簇。长江、黄河养育了世代中华儿女,也浇灌了璀璨的中华诗词,催生了星汉灿烂、光焰万丈的千古经典。
第一、长江黄河的壮丽风光,擘定了中华诗词的审美基础。千山同根,万水同源,山川之壮丽奇美,以长江、黄河为最。李白以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磅礴气势描绘黄河,又用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悠远意境擘画长江。宏阔的视野,浪漫的意气,豪迈的笔调,让我们在领略祖国山河之美的同时,欣赏到中国的诗词之美。黄河不仅有青铜峡大峡谷、石林、壶口瀑布、三门峡的恢宏壮观,也有“女儿湾”、九曲十八湾的蜿蜒秀美;长江滋养了富饶、美丽的江南水乡,但以劈开七百里三峡、跨越六千米落差的三级阶梯,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气壮山河,所以说黄河、长江同样壮美、秀美。古代诗人的笔下,“江山相雄不相让,形胜争夸天下壮”“水阔无边深无底,其来不知几千里”,描绘了山形水势之美;“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”“白发渔樵”“秋月春风”有色彩之美;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“山随平野尽,江入大荒流”是线条的美;“乱石穿空,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有构图的美;“江流宛转绕芳甸,月照花林皆似霰。空里流霜不觉飞,汀上白沙看不见”有光影交错的美,优美的文字与音乐、声响、节奏、韵律有机构成、相映成趣,在视觉之美、嗅觉之美、触觉之美、感觉之美中,表达或乐观豪迈、或愉悦张扬、或缠绵沉郁的情愫,各美其美,都是壮哉江河、大美中华的姿态。蕴含其中的美学价值、审美情趣、审美理念,擘定了中华文化的美学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审美取向。
第二、长江黄河的浩大气势,凝练了中华诗词的精神气质。黄河一路奔流,诗词一路芬芳。长江两岸,诗联词廊,风情万种。洞庭湖、鄱阳湖、太湖、巢湖四大湖与长江相通,满湖诗叶词花,一派争奇斗妍。长江有八大支流、700多条小支流、3600多条小小支流,还有4万多个湖泊和水库、无数的港汊溪塘。诗词流进情感的小河,乡愁荡起灵感的波光。一夜春风,万树梨花,每一瓣花开都是诗词在绽放,每一次绽放都是精神在张扬。一个没有文学精神的国度注定立不起、站不久,一个没有诗词翅膀的民族,注定飞不高、行不远。唐代诗人杜甫一生行走在黄河、长江岸边,游学于河南、山西、江浙、山东,先后与李白、高适同游汴州、梁宋、东鲁。“安史之乱”后,杜甫西走秦陇、南下巴蜀。47岁之前在洛阳、长安、华州、秦州、同谷,之后到剑南、成都、梓州。听说“安史之乱”被平定,杜甫高兴得泪流满面,写下“平生第一快诗”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“初闻涕泪满衣裳”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“白日放歌须纵酒,青春作伴好还乡”,而且马上启程,“即从巴峡穿巫峡,便下襄阳向洛阳”。人在长江,思念黄河,但无奈于贫病交加,沉重的步履沉重的心,沉郁顿挫的笔调写下“巫峡忽如瞻华岳,蜀江犹似见黄河”,心忧父老乡亲的安危甘苦。他辗转飘零在长江的嘉州、戎州、渝州、忠州、云安、夔州、江陵、岳阳、潭州,59岁时在长江荆楚之地的一条船上去世,葬于岳阳,后移棺河南巩义。杜甫的人生,沿着黄河、长江画了一个大大的曲曲弯弯的句号,但在黄河、长江两岸所亲历的颠沛流离的生活,成为对唐朝社会的感知和对底层百姓命运的体恤,成就了他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篇、“茅屋”篇等传世经典。风声雨声全入耳,涛声水声皆打心,黄河、长江流进了他的血脉,滋养了他关注国家、体察社会、体恤民众疾苦的情怀。长江、黄河培养了古代诗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凝成了中华诗词的精气神。

第三、长江黄河的宏阔境界,结构了中华诗词的天下格局。黄河流经九省份、长江流经十一省份,流域广阔,沿途留下大量诗词经典。唐代高适站在黄河岸边,面对收复青海九曲之后的和平景象,欣然赋诗:“青海只今将饮马,黄河不用更防秋”;王之涣在甘肃武威,抒发“黄河远上白云间,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豪迈之情;王昌龄站在宁夏的秋阳下低吟,“蝉鸣空桑林,八月萧关道,出塞复入塞,处处黄芦草”;三十年后,同样在宁夏的萧关道,还是在八月,岑参眼里是“凉秋八月萧关道,北风吹断天山草”。正是因为有了高适、王昌龄、岑参、王之涣这四位盛唐边塞诗人,中华诗词才充满了驰骋天地的血性与雄风;王之涣还在山西的黄河岸边,写下著名的《登鹳雀楼》,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,富有哲理的一句话,抬升了一个民族的视线高度。京杭大运河纵贯北南六个省份,在扬州与长江连通,长江、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钱塘江中国五大水系全部贯通,春江潮水连海平,经天纬地东到海,长江增添了中华诗词的天地英雄气、中华文化的天下情怀。岳飞的《满江红•怒发冲冠》“抬望眼”是高度,“仰天长啸,壮怀激烈”是气度,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是回望,更是展望,“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”是统一天下的抱负。另一首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,“遥望中原,荒烟外、许多城郭”“到而今、铁骑满郊畿,风尘恶”,满眼是伤痕,“兵安在?膏锋锷。民安在?填沟壑”,满心是伤痛,“何日请缨提锐旅,一鞭直渡清河洛”,是“还我河山”的壮志。岳飞从军二十载,在长江边上的武昌城驻扎七年,四次北伐中原、饮马黄河,是从长江起兵,黄河、长江是奔涌在他身体里的血脉。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是诗人的情怀;天下一统、金瓯永固,江山无恙、海晏河清是诗词的梦想与远方。毛泽东独立湘江岸边,“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”,看“鹰击长空,鱼翔浅底,万类霜天竞自由”“问苍茫大地,谁主沉浮”,到“万里长江横渡,极目楚天舒”,天地尽入怀。1936年2月在黄河岸边的陕西清涧县袁家沟,毛泽东写下《沁园春·雪》,1945年8月到10月的重庆谈判之后,11月14日的重庆《新民报·晚刊》发表了毛泽东的这首词,顿时轰动山城、波及全国,无不被这首来自黄河之滨的雄文所折服。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是视野的宏阔,“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”是气势的苍茫,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欲与天公试比高”是雄心壮志,“惜秦皇汉武,略输文采;唐宗宋祖,稍逊风骚”“一代天骄,只识弯弓射大雕”,是纵横历史天空、巡视寰宇风云的气概,“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,是民族自信与责任担当。转战南北、驰骋江河,让毛泽东主席从苍茫大地汲取了能量,毛泽东诗词也因此笔力雄健、意境旷达。这种境界,使中华诗词达到了新的高度。

第四、长江黄河的万千景象,铸就了中华诗词的高贵品质。文学的风骨看诗词歌赋,文人的风骨看点横撇捺。凡是经典之作,无一不是字斟句酌、惜墨如金,达到像南朝刘勰所说“捶字坚而难移,结响凝而不滞”的程度。一字拔山盖世,一句气象万千,一咏绕梁三日,中华诗词有高雅的格调、尊贵的禀赋,是中华文化的高地和圣地,却以平近的方式走进社会生活、走近平民百姓。旧时堂前燕,飞入寻常家,“黄口小儿初学行”“李杜诗篇万口传”,既观照现实,又为现实所需、被人民所用,才成就了自身的生命力。“黄河西来决昆仑,咆哮万里触龙门”,让你感受山河的气势和文字的力量;“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”,让你感受秋色的清凉与文字的高洁。元代诗人王冕夜宿黄河之滨,感叹说“水宿聊城外,忘眠听漏声。浮烟连野白,孤月近船明。世变山河在,时移草木惊”,从“水宿”“漏声”到“浮烟”“孤月”,再到“世变”“时移”,虚与实变幻交叠,动与静对比互衬,描摹了一个阔大的物理空间和精神世界,与唐代诗人张若虚的“江天一色无纤尘,皎皎空中孤月轮”“不知江月待何人,但见长江送流水”,有异曲同工、隔代共情之感,只不过唐月在前、元月在后,一个是春月、一个是秋月,一个在上半夜,一个在下半夜,都是对世界的观察、对世事的敏感、对世道的体悟,是中国文人内心的高光照亮。也许我们对王冕的理喻是多余的,因为他说了,“不要人夸颜色好,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高洁是诗词的品格,高贵是诗人的风骨,长江、黄河荡涤尘埃、洗尽铅华,让中华诗词有冰肌玉骨的品质、傲霜斗雪的品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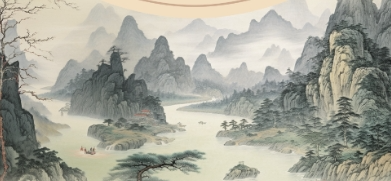
四大古老文明诞生于大河流域,但绵延至今,且以国家形态存在的,唯有中华文明。与其它三大古老文明相比,中华文明有一个独特的优势是,同时拥有黄河与长江两条大河源流、两个文化系统,相互形成竞争力和耦合力。地理上的“南江北河”,始祖认同上的“南炎北黄”,精神图腾上的“南凤北龙”,哲学思想上的“南道北儒”,文学艺术上的“南骚北诗”,物质文化上的“南稻北粟”“南丝北皮”“南釜北鬲”“南舟北车”等等,一直到今天的“南水北调”,形成了南北文化、江河文明的二元结构。这种结构既造就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,又使两种文化相互作用、相互融合,缺一不可。江河互通、南北共济,使中华文明获得了广阔、纵深的生长空间和回旋余地。江河文明因而熔铸成更加坚固的“合金体”、更加牢固的统一体。中华诗词正是这一文化现象、文化巨构、文化特色的鲜明体现和完美呈现,为中华文明经久不衰、历久弥坚,贡献了力量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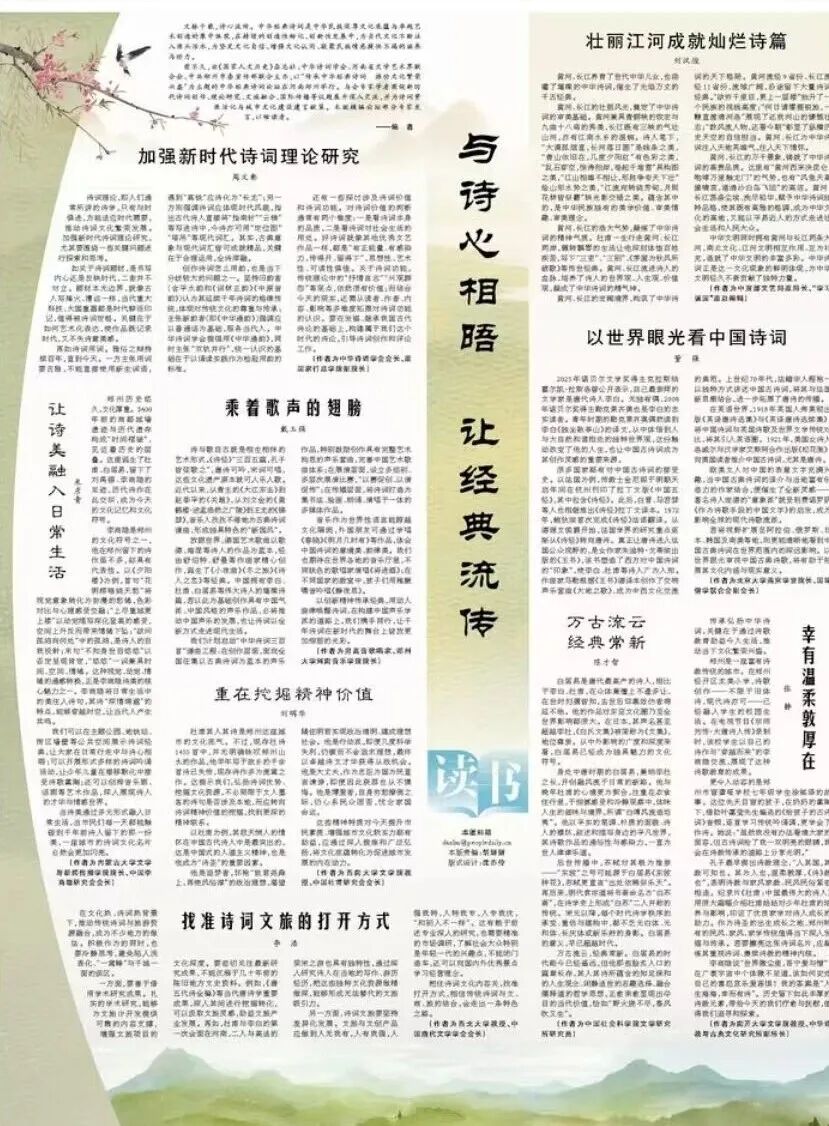
(原载2025年11月14日《人民日报》,刊发时有删节)